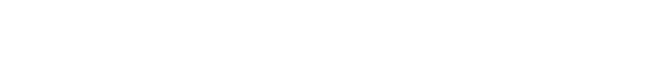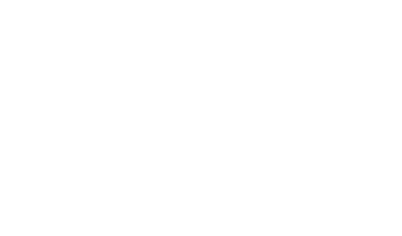《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第61条提出:“当事人达成的、具有给付内容的商事调解协议,经公证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或者经人民法院司法确认,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条表明了《合作区条例》支持和鼓励在合作区开展国际商事调解,但仍秉承我国司法传统对于调解协议效力谨慎保守的态度。合作区承担着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重大使命,应当充分利用其先行先试、制度创新的优势,探索谋求《新加坡公约》在我国的落地实施,完善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打造特色的跨境法律服务高地。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8月,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46个国家在新加坡签署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以下简称《新加坡公约》)。《新加坡公约》旨在解决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跨境执行问题,其核心内容是赋予国际商事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填补了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在执行领域的空白。我国作为该公约的首批签署国,面临着如何将我国的商事调解法律制度与之相衔接的问题。本文拟以我国现行商事调解制度的现状为切入点,结合《新加坡公约》内容,尝试对合作区商事调解制度的创新和优化提出可行建议。
二、我国现行商事调解的困境
一是我国目前暂无针对商事调解领域的专门立法。目前我国仅对人民调解进行了专门立法,制定了专门的《人民调解法》。而商事调解领域的相关规则散见于最高法司法解释性文件、“两高”工作意见以及各调解机构的调解规则中。此外,从我国调解立法的内容上来看,呈现出侧重诉调对接、案件分流以及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的规定,而相对忽视独立的调解制度规范。
二是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不足。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正当程序保障是执行力在程序法层面的正当性基础。概言之,不同于法院审判,由于民间调解员的资质和调解程序的正当性得不到绝对保障,因此我国理论界一般将调解协议的性质视为民事合同,认为调解协议不具有直接的执行力,并且符合撤销要件的调解协议能够被法院撤销,以实现司法权对调解协议的适度干预。
三是现有调解制度与《新加坡公约》尚不能衔接。《新加坡公约》规定了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直接执行制度,依据该公约,当事人可以请求缔约国的主管机关仅按照本国国内法规则和公约的规定强制执行商事调解协议,无需经过转化程序或者来源国的审查。也即,《新加坡公约》不允许对调解协议实体内容进行审查,这与我国现有制度安排是相冲突的。我国《人民调解法》第33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调解协议执行力的获得必须要经过人民法院的实质性审查。
三、合作区商事调解制度创新的展望
商事调解作为一种缓和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解纷成本低、保护商业秘密、维持商业关系等诸多优势,正逐渐成为各国商事主体解决跨境商事纠纷的首选方式。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三地在商事调解领域的合作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合作区肩负着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重任,要想营造趋同国际的高水平法治环境,亟须建立国际通行、具有先进性的商事调解法律体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赋予了合作区“率先在改革开放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大胆创新、先行先试、自主探索”的权限,可以通过变通立法、调法调规等方式实现商事调解制度的优化与创新。
从理论上说,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受到保障且程序正当的情况下,自治型纠纷解决结果应当具有执行力。《新加坡公约》确立的执行制度直接、高效,具有显著优势。为了促进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公约》能够尽快接轨,合作区可以率先推行试点,充分总结本区域内的商事调解实践经验,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商事调解制度,为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体系的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经验。本文认为,推动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公约》进行有效衔接可以遵循以下思路:
其一,推进专门的商事调解立法。针对商事调解立法框架的设计,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制订一部统一适用于国内、国际商事纠纷的调解基本法;另一种是主张制订“大调解法”,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纳入到统一的调解法之中;还有一种主张通过修改现有调解相关法律,将商事调解法律规范纳入其中;本文认为,制订一部统一的《商事调解法》是推动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公约》有效衔接的最理想方式,但立足于合作区的实际情况而言,采用“纳入式”的立法模式最为可行,亦即将商事调解规范作为专章纳入到合作区统一的纠纷解决规范之中。深圳在2022年3月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中,就是将商事调解规范作为“调解”专章中单独的一节予以规定。合作区可以参照这一做法,并将商事调解的直接执行制度纳入到该规范中,尝试在合作区范围内赋予符合《新加坡公约》条件下的国际和国内商事调解协议以同样的执行力,同时对调解员的任职资格和行为规范也可以在规范中作出明确规定。
其二,强化湾区示范规则的指导作用。广东省先后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标准》《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专业操守最佳准则》和《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争议调解示范规则》已初步构建起大湾区商事调解的制度体系,为三地调解机构制定详细调解规则时参照适用提供了范本。《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争议调解示范规则》是在充分借鉴《新加坡公约》、联合国贸法会调解规则、香港调解条例以及粤港澳三地知名调解机构调解规则的基础上制定,兼顾了粤港澳三地在商事调解操作规程方面的差异。强化示范规则对商事调解机构制定调解规则的指导作用,能够促进三地调解规则的统一。
其三,促进湾区商事调解组织的协同发展。粤港澳三地法律规则差异大、制度藩篱多,三地之间应当通过强化商事调解组织的交流与协作,逐步构建起调解组织的常态化交流和调解员培育机制。合作区在涉外商事案件审判中,可以引入港澳籍商事调解员,实行“内地+港澳联合调解机制”;建立跨境调解联盟合作平台,在调解组织中引入商事调解领域专家学者和资深律师等;将这一系列措施常态化、规模化推进,强化粤港澳三地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构建起服务“一带一路”的区域性法律服务和纠纷解决中心。
参考文献:
1. 王宇石:《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商事调解制度的优化与创新——以<新加坡公约>为背景》,载《求索》2022年第5期。
2.赖来焜:《强制执行法总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87页。
3.文金羚:《<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研究》,载《商事仲裁与调解》2022年第5期。
4.唐琼琼:《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载《上海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5.廖永安:《关于我国统一“调解法”制定中的几个问题》,载《商事仲裁与调解》2020年第2期。
6.刘敬东、孙巍、傅攀峰等:《<新加坡调解公约>批准与实施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2页。